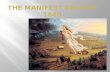335 清華中文學報 第十四期 2015 年 12 月 頁 335-373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 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 黃錦珠 ** 摘要 清末女權思潮乍興,女子開始走出閨閣,拓展更寬廣的行動幅 圍,擁有新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繼續受制於深重的父權社會傳統。小 說原屬於傳統文學版圖的邊緣文類,於清末民初時期躍居文學主流。 女作者原居於文壇的邊緣位置,也在清末民初時期逐漸向文壇中心移 動。清末民初,逐漸增多的女作者躍上文壇,藉小說發出婦女的聲音。 當女作者的寫作文類,從傳統的詩、詞、文、賦,發展為具有通俗色 彩的小說,這種移動所帶來的,不僅是寫作文類的不同、作家身分的 多元,同時還有作品流播方式與作家現身方式的移轉。有趣的是,女 作者小說中,對於女性人物的所處空間與移動、移動所帶來的身分流 轉,乃至參與世界、建構主體的方式,也呈現多元多姿的想像與描述, 一方面折映了現實婦女的時新際遇,另一方面又再現了女作者的主體 感知。不同空間所代表的行為意義、移動所引發的身分流轉,以及涉 入公共領域所呈示的自我形象,無論發生在小說內部或是小說外部, 都提供了很好的鑑鏡,可據以觀察清末民初女作者所建構的世界觀與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3-2410-H-194-086-MY3 之部分成果,初稿曾於 2015 年 6 月 15-16 日愛丁堡大學主辦,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Dimensions of Mobility: Travel and Adventure i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會上宣讀,此為修改 稿。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Welcome message from author
This document is posted to help you gain knowledge. Please leave a comment to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Share it to your friends and learn new things together.
Transcript
335
清華中文學報 第十四期
2015 年 12 月 頁 335-373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
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黃錦珠**
摘要
清末女權思潮乍興,女子開始走出閨閣,拓展更寬廣的行動幅
圍,擁有新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繼續受制於深重的父權社會傳統。小
說原屬於傳統文學版圖的邊緣文類,於清末民初時期躍居文學主流。
女作者原居於文壇的邊緣位置,也在清末民初時期逐漸向文壇中心移
動。清末民初,逐漸增多的女作者躍上文壇,藉小說發出婦女的聲音。
當女作者的寫作文類,從傳統的詩、詞、文、賦,發展為具有通俗色
彩的小說,這種移動所帶來的,不僅是寫作文類的不同、作家身分的
多元,同時還有作品流播方式與作家現身方式的移轉。有趣的是,女
作者小說中,對於女性人物的所處空間與移動、移動所帶來的身分流
轉,乃至參與世界、建構主體的方式,也呈現多元多姿的想像與描述,
一方面折映了現實婦女的時新際遇,另一方面又再現了女作者的主體
感知。不同空間所代表的行為意義、移動所引發的身分流轉,以及涉
入公共領域所呈示的自我形象,無論發生在小說內部或是小說外部,
都提供了很好的鑑鏡,可據以觀察清末民初女作者所建構的世界觀與
* 本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MOST 103-2410-H-194-086-MY3 之部分成果,初稿曾於
2015 年 6 月 15-16 日愛丁堡大學主辦,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Dimensions of Mobility:
Travel and Adventure in China’s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會上宣讀,此為修改
稿。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清華 學報
336
主體意識。本文將以清末民初計十五位女作者的小說為研究材料,觀
察女作者小說中女性人物的所在空間與移動敘述,兼及小說文本的問
世、傳播方式,探析小說內外的移動現象及其意義,希望能揭顯其中
所蘊含的空間意識與世界觀、性別認知與身分主體。
關鍵詞:清末民初、小說女作者、移動、空間、身分、公共再現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37
一、前言
中國文學史上已知的女小說家,數量遠遠少於女詩人、女詞人
等,小說女作者出現的年代也遠遠晚於詩文女作者。目前可見且確定
為女作者所寫的小說, 早是顧太清(1799-1877)《紅樓夢影》,出
版於清光緒三年(1877),署名「雲槎外史」,雖有序文(署名「西湖
散人」),卻缺乏對小說作者與作序者的相關介紹,顯然無意披露彼此
的真實姓名與性別、身分。當時視小說為文學末流,不入大雅之堂,
序文與小說作者有意無意隱藏自己的真實身分,可以說是一種常態。
光緒二十八年(1902)開始,「新小說」浪潮席捲文壇,小說地位提
昇,作家數量大增。這一階段,小說逐漸入據文壇主流,女作者也參
與了這項文學大業。目前已知清末 早發表「新小說」的女作者,是
王妙如(1878?-1904?),她所寫的《女獄花》(1904)以描述女界
革命為宗旨,呼應了清末女權的新思潮。小說署名「王妙如」,以真
實姓名示人,也顯示了新的小說觀念與寫作身分認同。這部小說的出
版,上距顧太清《紅樓夢影》,已達二十七年。清末民初(1840-1919)
這一小說觀念、地位乃至寫作型態都產生劇變的階段,究竟有多少女
作者參與創作,寫出多少小說,這恐怕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現有
的文學史或小說史,也大都忽略了這個問題。此階段之女小說家至今
晦隱難明,時間的沖刷汰洗,固然是因素之一,而無所不在之性別機
制所導致的女作者之邊緣處境,恐怕也是難以追查探究的重要因素。
清末女權思潮乍興,女子開始擁有新的發展空間,同時也繼續受
制於深重的父權社會傳統。清末民初已然出現不少先進婦女,參與公
共事務,行走世界異國,不過,整體的社會習氣,仍墨守男外女內的
傳統規範。絕大多數的婦女,包括數量漸增的女知識份子、女作者,
仍然背負沈重的傳統包袱。當主要生活於閨閣或者開始踏出閨閣的女
作者從事小說創作,出現在她們筆下的虛構世界,是否不同於生活空
清華 學報
338
間一向寬闊無限制的男作者?清末民初,逐漸增多的女作者躍上文
壇,藉小說發出婦女的聲音。當女作者的寫作文類,從傳統的詩、詞、
文、賦,發展為具有通俗色彩的小說,這種移動1 所帶來的,不僅是
寫作文類的不同、作家身分的多元,同時還有作品流播方式與作家現
身方式的移轉。有趣的是,女作者小說中,對於女性人物的所處空間
與移動、移動所帶來的身分流轉,乃至參與世界、建構主體的方式,
也呈現多元多姿的想像與描述,一方面折映了現實婦女的時新際遇,
另一方面又再現了女作者的主體感知。不同空間所代表的行為意義、
移動所引發的身分流轉,以及涉入公共領域所呈示的自我形象,無論
發生在小說內部或是小說外部,都提供了很好的鑑鏡,可據以觀察清
末民初女作者所建構的世界觀與主體意識。本文將以清末民初計十五
位2 女作者的小說為研究材料,觀察女作者小說中女性人物的所在空
間與移動敘述,兼及小說文本的問世、傳播方式,探析小說內外的移
動現象及其意義,希望能揭顯其中所蘊含的空間意識與世界觀、性別
認知與身分主體。
清末民初以「女士」或「女史」署名的小說其實經常可見,但此
中可以確定為女作者的,卻寥寥無幾,而且困難重重。由於當時男作
者有不少化名為女士、以女士為筆名的現象,因此若沒有其他資料佐
證,逕以「女士」或「女史」署名者為女作者,很可能就會謬誤百出。
然而女作者的傳記資料,無論是正史、方志或野史、筆記,都可以說
極端稀少而且難以尋找。社會與文壇上深遠的男權文化,女作者長期
1 本文所謂「移動」,是一種根本性的基礎概念,包括具體的移動,例如走動、外出、旅行、
遷移等,也包括抽象的移動,例如身分屬性、人際關係、社會階層等,甚至可以說,移動
性無所不在。〔英〕彼得‧艾迪(Peter Adey)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新北:群
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頁 1-43。 2 其實截至目前為止,清末民初可以確認的女小說家約近二十位,但因其中部分作品尚未蒐
集齊全,不便納入討論。本文選擇其中十五位女作者的小說做為討論對象,數量比例達四
分之三,應已具有相當代表性。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39
所處的邊緣位置,都使得她們的傳記資料罕有記述、留存者。根據筆
者近年蒐集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及其資料所得,截至目前為止,可以
確認為女作者的近二十位,長、短篇小說共有數十種,與當時龐然大
量的男作者及其小說相較,誠然比例懸殊。本文選擇其中作品比較齊
全的十五位女作者之小說,做為觀察與討論對象。雖然女作者小說數
量有限,但在女權初興、女作者逐漸在文壇公開發表與活動的清末民
初時期,這樣的數量已經頗為可貴,而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末民初這十五位女作者可以明顯區隔為三個世代,數量由少而
多,呈向上提升之形,可視為女作者漸次顯露而立足於文壇的發展曲
線。《紅樓夢影》作者顧太清屬於第一個世代,在鴉片戰爭(1840)
之前出生、成長,基本上還未受到女權思潮的洗禮。第二個世代的女
作者,大多出生於十九世紀七○至八○年代,如王妙如、邵振華
(1881-1924)、黃翠凝(1875?-1917 後)等三位。她們出生之時,
西方思潮已經逐漸進入中國,只是規模或數量都還有限。她們很可能
大都接受傳統的女(塾)學教育,女權思潮大約在她們長成以後開始
盛行。她們或許不是 前衛的先進婦女,卻已經接受某些女權主張,
小說中也可看到或多或少的女權議題,所撰小說主要發表於清末 後
十年間,少數發表於民國初年。高劍華及其他《眉語》女作者為第三
個世代,計有十位,多數接受過新式女學堂教育,民初時期才開始寫
作、發表。此外,呂韻清(1870?-1937 後)可視為橫跨第二與第三
世代之人,她的出生、受教、成長,屬於第二世代,晚清時期她是女
詩人、女畫家、女教員,進入民國以後開始發表小說,與第三世代的
女作者同時現身於小說界,成為多產的女小說家之一。她或許可以成
為連繫第二、第三世代女作者的鮮明案例。這三個世代的女作者及其
小說(詳附錄一),3 展現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移動現象及意藴,
3 這三個世代共計十五位女作者,都曾經透過生平考察或者照片確認其身分,可參黃錦珠,《女
清華 學報
340
值得深探!
二、從閨閣到世界:小說的女性空間與行動幅圍
縱觀三個世代的女作者小說,很容易辨認出一種行動或移動的發
展軌跡,那就是從家庭、閨閣,也就是「正位於內」的傳統女性空間,
逐漸向廣闊的家外空間,包括異鄉、異國,乃至世界、全球延伸。當
然,這個發展軌跡不是順暢無礙的直線大道,而是佈滿各種曲折、迴
轉的彎道以及凹凸不平的坎洞。
顧太清《紅樓夢影》中,人物的主要活動空間,幾乎都在家庭內
部。小說接續《紅樓夢》原故事的尾端,從毗陵驛賈寶玉雪中拜別賈
政寫起,它翻轉了原書的結局,賈政一見到寶玉與一僧一道,立即喝
叫眾家人捉拿,拿住僧、道二人並送官究辦,救回寶玉,返回北京。
賈府從此一家團圓,蔣玉函也送回襲人,賈寶玉妻妾圓滿,賈府喜事
連連,寶釵生子,平兒扶正、生子,賈政拜相,而後致仕。王夫人、
薛姨媽、邢夫人等就在子孫環繞的家庭生活中和樂過日。王夫人、薛
姨媽疼愛兒孫,自不必贅言,邢夫人也變得規矩仁慈,與眾人和諧相
處。王夫人、薛姨媽幫寶釵、平兒準備生產需用物品,坐月子,帶小
孩,種種生活瑣務,婆媳、母女相互照顧。薛寶釵與平兒本是大方隨
和之人,與上下人等相處和諧,寶玉、賈璉妻妾同心度日。寶玉原就
具有體貼女兒的性格,賈璉也變得安分守己,善體人意。4 故事中時
時可以感受家庭溫暖,小說也以描述和樂溫馨的家庭生活為重心,人
物的活動空間絕大部份都在賈府府內,尤其是女性人物,不見外出或
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4 年),第 1、2、3、
8 章,頁 1-88、209-244。 4 〔清〕雲槎外史(顧太清),《紅樓夢影》,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4 冊,第 1-24 回,頁 1-444。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41
遠遊的情節,5 即使提到出嫁的女兒,也經常一句「接了探春回來」
或「把巧姐接了過來」6 等簡單帶過,便進入賈府室內空間的生活事
件描寫。第一個世代的顧太清《紅樓夢影》雖是孤例,但是小說的敘
事空間符合傳統女性生活空間,可視為慣例常態之表現,也足以代表
傳統女作者的空間感知與想像。
第二個世代的女作者小說,例如王妙如《女獄花》、邵振華《俠
義佳人》,其中女性人物遊歷國內各地或者遊學異國的描述不但增
多,而且顯得理所當然。《女獄花》的沙雪梅經歷出嫁、殺夫、入獄
等事件,為了鼓吹女界革命,組織武裝力量,不但從獄中逃離,而且
號召同志,奔走各地。許平權則主張和平革命,與同志董奇簧留學日
本,遊歷美、歐。7 小說對於國內地名多是模糊帶過,例如稱沙雪梅
所居之地為「這國的東南的東鄉」,8 倒是寫及許、董二女遊學海外
時,日本的長崎、東京、法國的首都巴黎等,9 寫得清楚明確。藉由
這些晚清聞名的異國城都,展示了女子走向世界的開闊意圖。《俠義
佳人》中,有親歷全國各地,四處演說,宣揚女權與文明學說,乃至
拯救危難婦女的「曉光會」成員,如會長孟迪民、顧問高劍塵、副會
長田蓉生、會員華澗泉、孟亞卿等,也有留學異國,東洋、西洋遊走
的知識女傑,如蕭芷芬、孟澹如等。她們分別到過山東、湖南、江蘇、
浙江等省份,在濟南「金村」、上海、江陰、梧城等城鎮興辦女學堂
或舉行演說會,出洋者則多是前往日本、美國,或說成美洲、歐洲,
其中 具體的該是指名美國紐約以及「紐約女子大學」。10 這些分佈
5 參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148-149。 6 〔清〕雲槎外史(顧太清),《紅樓夢影》,第 5 回,頁 72、81。 7 〔清〕王妙如,《女獄花》,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百花洲文藝出
版社,1993 年),第 64 冊,第 1-12 回,頁 701-760。 8 同前註,第 1 回,頁 710。 9 同前註,第 10 回,頁 749。 10 績溪問漁女史(邵振華),《俠義佳人》,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大系》(江西:百
清華 學報
342
於海內外的地點名稱,無論是取自現實還是明顯虛構,主要展示了女
作者廣闊的地理知識與空間想像。雖然清末時期有機會遊歷海外異國
的婦女已經頻頻出現,目前所知的第一部中國婦女出國遊記:單士釐
《癸卯旅行記》(1904),其出版問世時間也不晚於這批女作者「新小
說」,11 但根據目前有限的生平資料,王妙如、邵振華、黃翠凝等第
二世代的女作者,很可能並沒有實際出國經驗,12 不過,無論女作者
是否擁有親身遊歷的經驗,其世界觀與時俱進,地理知識與眼界之開
闊,已非昔日靜守閫域的閨閣婦女所能比擬。
除了叫得出名稱的都城、國家,比較值得注意的,其實是人物活
動的具體空間與場景。第二個世代的女作者小說,無論《女獄花》、《俠
義佳人》,還是《姐妹花》,雖然小說中出現異地、異國、異洲等地點
名稱,女性人物也經常外出、移動,但主要的活動場景大半仍在家庭、
學堂、會議廳或講堂等室內空間。那些遠方的異地異國,大多數用來
交代人物離場的去處,或用以說明學識經歷的來處,總之多已成為並
非現場的「他方」。小說中發生於室內空間的事件,遠多於發生在室
外空間的事件。室內空間的人物活動,例如演說、會議、聚會或宴會、
上課、談話、閱讀、書寫、觀賞、日常家務等等,所占篇幅遠遠多於
上街、出遊或者在外辦事。小說整體讀下來,仍覺得靜態多於動態,
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第 64 冊,第 1-40 回,頁 83-699。引文見第 28 回,頁 457。
以下引用此書文字,除非特別註明,概皆出於此一版本。 11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現知版本為 1904 年日本同文印刷舍所印,這很可能就是早的印本。
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冊 5,頁 681-755。鍾叔河
〈第一部女子出國記〉一文對此書有扼要的說明,亦收入該書,冊 5,頁 657-679。 12 王妙如約二十七歲左右便逝世,其夫羅景仁強調她「性質聰慧,且嗜書史」,「予每自負得
閨房益友」,被描述成安處閨閣的傳統才女形象。邵振華在安徽績溪成長,嫁入浙江桐鄉勞
家為長媳,她的公公勞乃宣游宦異地時,她與丈夫勞炯章大多時候留守夫家故居。黃翠凝
身為寡婦,曾寄居上海,賣文為生,但生活窘迫,當無財力出國。參羅景仁,〈跋〉,收入
王妙如,《女獄花》,頁 760;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
頁 15-16、26-30。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43
人物活動的「現地」,由家庭內部或室內空間佔據主導位置。呂韻清
小說也有這種現象。在這一點上,她是比較趨近於第二世代女作者的。
第二世代女作者小說中,少數把異國都城做為「現地」場景來敘
寫的,例如《女獄花》,曾經描述許平權與董奇簧遊歷巴黎的情景,
道:
不知不覺到了法國巴黎。坦坦大道,全體敷石,車輪行過,一
些聲息也沒有。且常有人拿著香水,到處敷灑。13
文中有關巴黎街道場景的描繪,車輪無聲或噴灑香水,意圖透過寧靜
與氣味,凸顯法國首都的文明與不凡,卻不免有誇飾失實的嫌疑。這
種過度美化的想像,彰顯了女作者對於法都巴黎與西方文明的十足憧
憬。對於晚清時人而言,法國是「自由」誕生的母國,小說所述:「平
權心內想道:法國是自由發生的地方。果然與別國不同。」14 表露了
對於法國與巴黎的嚮往。這種嚮往,是身處自居落後的中國,對於難
以企及的遙遠異國所生的想望。也就是說,小說中的人物,經過越洋
移動到了法國,但寫作視角的定位點其實仍停留在中國。對於異國都
城的描述,是著眼於中國尚未企及的文明氣象。透過小說人物的移動
路徑,遍及亞、美、歐各州的跨洋行蹤,女作者一方面展現了對遼闊
世界版圖的地理認知,另一方面傳達了對於朝向西方、走向世界的極
度推崇,再一方面也洩露了自己實際遊歷的不足。第二世代的女作
者,多數在傳統的教育與社會體制中成長,遠途旅行或遊歷的實際經
驗其實不多,自由度也還不充分,小說人物的跨洋移動,雖足以呈示
13 〔清〕王妙如,《女獄花》,第 10 回,頁 749。 14 同前註。法國大革命一事,使巴黎成為舉世聞名的自由誕生地,小說所流露的嚮往之情不
難理解,只是此中主觀想像的成分也不宜忽視。〔法〕帕特里斯‧伊戈內(Patrice Higonnet)
著,喇衛國譯,《巴黎神話:從啟蒙運動到超現實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頁
50-79。
清華 學報
344
女作者的開闊胸襟與企圖,卻免不了出現想像失實的描寫細節,但無
論如何,世界觀之開放是在第二世代女作者小說中便已經浮顯的事
實。
第三個世代的女作者,例如高劍華及其他《眉語》女作者,筆下
的女性人物出外行走,無論是為了求學、工作、尋親或者追求所愛行
蹤,也無論是異鄉異國,越洋跨洲,都已屬頻繁常見之舉。例如梁桂
珠(?-?)〈同氣連枝〉寫到「妹」「渡洋而西,至新大陸學美術畫
焉」,15 高劍華《梅雪爭春記》16 寫梅珠與雪玉二姐妹,為了追尋所
愛,從美國到歐洲的英國、法國等。17 孫青未(?-?)〈儂之心〉寫
男、女主人公曲折多變的婚戀故事,從法國而英國,遍經湖上、海上、
都市、鄉間甚至戰場,靡所不至。18 與第二世代的女作者小說相較,
出國留學的學習門類有了較為個人化的考量與具體的項目,更重要的
是,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等都城的街道、公園、建物乃至郊區、鄉間,
種種具體空間,屢屢成為小說人物的活動地點,不僅僅是小說中人物
離場前往的地名而已,呈顯了更為具體可觸的實地認知或想像。名都
風貌與世界版圖不再是遙遠的「他方」,而是當下現在的「此地」。所
寫都城也未盡是美好的一面,例如姚淑孟(?-?)〈郎歟盜歟〉提到:
「都會愈繁盛,則盜賊愈充塞,世界各國所同病也。在歐洲秘密社會
15 梁桂珠,〈同氣連枝〉,載於高劍華主編,《眉語》第 2 號(1914 年 12 月),收入天龍長城文
化藝術公司編,《民國珍稀期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年),冊 1,
頁 223。 16 《梅雪爭春記》於 1915 年 11 月至 1916 年 4 月在《眉語》連載之時署名高劍華,《眉語》
停刊以後,《梅雪爭春記》於 1916 年 7 月由新學會社出版單行本,署名則是許嘯天。馬勤
勤據此認為《梅雪爭春記》為許氏之作(馬勤勤,〈作為商業符碼的女作者──民初《眉語》
雜誌對「閨秀說部」的構想與實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 年第 5 期,頁 151-159),
但筆者以為此中作者問題尚有待進一步釐清,故此處仍據《眉語》所署,以高劍華為作者。 17 高劍華,《梅雪爭春記》,《眉語》第 13 至 18 號(1915 年 12 月至 1916 年 4 月),冊 7-9,
頁 2855-3977。 18 孫青未,〈儂之心〉,《眉語》第 3 號(1915 年 1 月),冊 2,頁 433-458。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45
之多,無過於巴黎、倫敦」。19 指出名都大城固然有繁華富盛的一面,
也同時充塞髒污危險的因子。可見女作者不再一廂情願彰顯首府名都
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優越先進,而能夠觀照其中的優劣得失,比較貼
近現實狀況的多元多樣。
與此同時,《紅樓夢影》提及的交通工具,僅見舊式的轎子、馬
匹、轎車或馬車等,《女獄花》則已出現輪船、火車,《俠義佳人》則
在近處移動時使用過轎子,遠方移動時搭乘火車、輪船等新式交通工
具。第三世代的女作者小說中,人力車、新式的馬車、火車、輪船而
外,舊式的轎、馬,已經不見蹤影。三個世代的小說中,外出、遠行
所需的交通工具由舊而新,時代、社會景況之變化,於小說中映現出
可辨的軌跡。新式交通工具的逐漸普及,不但使得人物行動力大幅提
升,大型運輸工具本身所提供的半開放/封閉空間,也讓女性人物有
更多與陌生大眾雜處的機會。傳統閫域、男女之防的突破,在這樣的
時空中默默進行。《女獄花》曾寫及許平權由巴黎返國,在輪船上「長
噓短嘆」,旁邊少年(黃宗祥)因關心而動問。對於黃宗祥的搭訕行
為,許平權一開始「正色」指斥他說話「輕薄」,「一些道德心也沒有」,
後來記起曾經在東京留學生會館見過兩次面,才陪笑道歉。20 這個事
件使許、黃二人結為同志,多年後又結為夫婦。由小說所述這個細節,
可以窺見外出旅行、游學等移動行徑,同時牽引出更多複雜的社會行
為與人際關係之變化。女性人物在(半)公共空間,既有自我警醒的
高度戒心,也勇於接受新的人際或機會。小說中這個事件的美好結
局,隱示了空間開放、男女社交公開利大於弊的想望。
《女獄花》船上搭訕一事,觸及了「道德」問題,其實第二世代
女作者小說,例如邵振華《俠義佳人》、黃翠凝《姐妹花》等作,對
19 姚淑孟,〈郎歟盜歟〉,《眉語》第 3 號(1915 年 1 月),冊 2,頁 425。 20 〔清〕王妙如,《女獄花》,第 10 回,頁 751。
清華 學報
346
於女性人物外出,不時明指或暗示要有僕伴同行,家庭以外的公共或
開放空間,潛藏不少對於單身女子的安全與道德疑慮。21 然而第三世
代的女作者小說中,女性人物無論出於被動或主動,外出或遠遊,大
體都與男性人物一樣的自由、自如,除了少數特定區域,例如知識階
層不高、男女工人混雜的工廠附近,仍潛藏威脅青年女子人身安全的
危險因子22 外,單身女子外出獨立行動的疑慮,基本上已經淡化。女
性人物的行動自由與開放空間的安全感,有明顯的提升現象。第三世
代女作者小說中,發生於室外空間的事件也明顯增多,包括遠地旅
行、鄉間或公園遊憩、車站或街上往來迎送、游泳與競走等室外運動
或技能、廣場上的武術與賣藝、發生於近海的海難、行軍隊伍與沙場
戰事等等,室外事件與場景不但多樣多姿,所佔篇幅、比例也更大,
人物移動頻繁,小說整體的動態感顯著提升。
宏觀來看,時代巨輪的碾動,推促了女作者小說中移動之發生。
小說中,女性人物由室內朝向室外,從家庭邁向世界的舉動,是以時
移世變的巨型移動為基石而完成的。女作者自身的移動經驗也隨著社
會型態推移而越來越頻繁、越開放,同時逐漸獲得合理化與正當性。
不能否認的是,女性移動的方向、範圍、幅度,仍然有別於男性。移
動過程的個人顧忌、疑慮,依然映現諸多女性限制。但是,胸懷世界、
放眼全球的空間意識與移動感知,正在點滴積聚,且緩緩凝塑成形。
女作者分別透過知識、想像、實際經驗等,在各自的小說中摹繪了屬
於當下與未來共構的移動性。
21 參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149-151。 22 許毓華,〈一聲去也〉曾寫到女主人公羅蘭在工廠附近遭「惡少」調戲。《眉語》第 1 號(1914
年 11 月),頁 14-15。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47
三、從妻女到女傑或女工:小說的女性身分與際遇流動
「男主外,女主內」的久遠觀念,以及「男有分,女有歸」的傳
統古訓,界定了男女有別的社會分工與人生角色,也深刻影響了男女
不同的移動方式與目的。中國歷代小說,乃至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
中,很容易看到大多數的男性人物,為了求學、遊歷、經商、謀職,
包括出仕、遊宦而移動,傳統的女性人物則大多因出嫁而移動。無論
基於何種因素,移動一旦發生,往往伴隨際遇的變換與身分的流轉。
以傳統婦女的常例來說,女子一旦出嫁,主要生活空間從母家轉移到
夫家,其身分也從為人女,擴轉而為人妻、為人媳,並預示將來為人
母的角色。顧太清《紅樓夢影》的女性人物,除了丫鬟、僕婦、乳母
等,乃基於賣身或聘僱關係而出入賈府外,無論嫁出的女兒或嫁入的
媳婦,從花襲人被送回賈府算起,到蔡小姐嫁與賈環為妻,泰半依循
這樣的人生歷程,罕有例外。從第二世代的女作者小說開始,出現了
因求學、追求志業等因素而移動的女性人物。王妙如《女獄花》中,
沙雪梅原先依循傳統軌範,由父親作主訂下親事,過門成婚,由人女
成為人妻。後來失手打死冥頑守舊的丈夫,自首入獄,從身懷武藝的
良家婦女變成殺人女犯。接著越獄逃亡,決心戮力推翻男權,爭取女
權,為女界革命獻身,再由女囚、逃犯轉變成女志士、女革命家。23 監
獄,是沙雪梅從普通婦女轉變成為革命女傑的過渡空間。監獄所藴含
的違法犯紀、背離常軌性質,不但應和小說情節的發展,對於沙雪梅
此後的新身分與人生角色也深具隱喻意涵。進出監獄的移動行為,改
變了沙雪梅的社會身分,也扭轉了她的人生軌道方向,充滿了跨界重
構的行動意蘊。透過她的行動與意志的描述,女作者展現了面對女性
處境的主體感知與移動意識。當沙雪梅以女界革命志士的身分開始移
23 〔清〕王妙如,《女獄花》,第 1 至 9 回,頁 709-747。
清華 學報
348
動以後,所勾連出場的人物,也大都是目標相近的新式女性,例如終
身不嫁、著書醒世的文洞仁,對醫學深感興趣的董奇簧,開設女報的
張柳娟,以及主張採取和平手段、以興女學為當前要務的許平權。文、
董、張、許諸人,除了同為致力重構男女權力版圖的女志士,也分別
是女文人、女報人、女醫師、女學生、女教員與女校長。女性人物的
身分多元化了,得以出入遊走的空間也更為廣闊而多樣,其人生軌道
與志業目標同時出現更多不同的方向與選擇。從這裡可以看到的,既
是行動空間的擴展、移動方式與目的的改變,同時也是人生際遇與社
會身分的轉換。邵振華《俠義佳人》中,行走全國各地的「曉光會」
成員,以演說家、調查員的身分四處宣導女權,調查女界現狀。各式
各樣的女性人物,包括傳統的家庭婦女與新式的女學生、女教員、女
校長、女會長、女顧問、女書記、女演說家等輪番上場,平實陳列了
新舊女性的各種身分角色與際遇流轉。新舊之間的界線,雖然不是涇
渭分明,然大體而言,僅具為人妻母之單純身分者,以守舊無知的「野
蠻」形象居多,具有新式女性身分者,開明進步的「文明」形象居多。
小說有意對舉新/舊、進步/落伍、改革/保守、文明/野蠻等二元
分立的價值模塑,以求傳達維新改革、提倡女權的意蘊,這也可說是
第二世代女作者回應女權思潮的方式。
「新女性」的移動能力、幅度與範圍,不僅展現於地方、國家、
洲際等有形的物理空間,也展現於知識程度、職業身分、道德人品等
無形的社會階層、人格範疇與人生軌跡。回到理想色彩濃厚的《女獄
花》來看,沙雪梅為了提倡女權,決意聯絡同志,從事流血革命。她
不但以殺夫的激烈手段,毀棄為人妻的傳統女性角色,而且以自覺自
勵的方式,鼓舞自己成為革命女傑。由為己而為人,從關心自己到胸
懷女性全體,意圖為所有女同胞追求權益,開闊的關懷空間凝塑了卓
越不凡的人物形象。 後革命失敗,正在巴黎遊歷的許平權在報紙上
讀到了這個消息: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49
奇簧走到平權身邊,見報紙上已滴著許多淚珠,仔細將報一
看,裡面載著女界革命黨首領沙雪梅因大事不成,同其友張柳
娟等七十餘人自焚而死。奇簧看到這裡,亦淚如泉涌。24
董、許二人,都是有志倡導女權的知識女性,讀到報紙所載信息以後,
董奇簧決心從巴黎轉赴美洲繼續深造,許平權則立即返國,從事興女
學的工作。這個細節構築了女作者對於公共媒體無遠弗屆的高度想
像,也建構了女性人物進入媒體報導的偉大形象。這部小說以宣揚女
權為宗旨,雖然不完全認同激烈的革命手段,卻依舊肯定激烈手段的
可能功用,並將沙雪梅描述成奉獻犧牲的女英豪,同時利用報刊的傳
播,肯定了這個形象的價值。報刊,這個透過文字傳輸的印刷載體,
形成一種面向大眾開放的言論空間。清末時期,報刊不僅在數量上大
為繁盛,也在輿論界形成不可忽視的一大力量。小說中,以之成為紀
錄革命志士事蹟與下場,並改變其他兩位女志士的既定行程與移動軌
跡,既彰顯了報刊的能動性與宰制力,也形塑了傑出女性與公共媒體
的互涉關係。梅嘉樂(Barbara Mittler)曾經指出,大約一八八○年
代開始,媒體已經開始倡導將女性公眾人物視為主體,然而自一八七
○年代直至一九一○年代,報刊的許多論說文字和新聞報導卻仍將她
們視為客體,試圖將她們限制於特定的女性化角色。25 其實不僅報刊
媒體,現實社會中,婦女想要獲得主體性仍存在諸多窒礙,26 然而在
虛構的小說空間,女作者已經為女性主體的呈現、確立與公眾對待,
24 同前註,第 10 回,頁 750。 25 〔 德 〕 梅 嘉 樂 著 , 孫 麗 瑩 譯 ,〈 挑 戰 / 定 義 現 代 性 : 上 海 早 期 新 聞 媒 體 中 的 女 性
(1872-1915)〉,收入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縣:左岸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年),頁 255-287。 26 呂芳上也曾經指出:「婦女運動一旦變成『運動婦女』,以婦女自身作為一個社會獨立自主
人格的『人』的要求,便不易再被重視」。參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收入陳三井
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第 2 章,頁 254。
清華 學報
350
想像出可貴可親的願景。沙雪梅從武術世家的女兒,起先遵守傳統軌
道,成為人妻,後來人生發生重大轉折,先成為女囚、逃犯,接著蛻
變成為革命志士, 後更因革命而犧牲性命,成為「拋頭顱,灑熱血」
的英勇女傑。報刊對她的報導,代表了蓋棺式的論定,替她的身分給
予定位,也寓示她一生際遇的價值。下場雖然不幸,肯定意義卻無可
置疑。許平權知道她的消息以後,回國興辦女學堂,努力十餘年,也
終於達成昌明女界的理想,並完成自己的婚姻,27 既兼顧了女知識份
子、女志士的使命,也滿足了為人妻的傳統目標。透過沙、許二人的
不同努力與選擇,小說映示了女性可能生發的主體力量。她們的移動
能力、幅度與範圍,不僅展現於地方、國家、洲際等有形的物理空間,
也展現於知識程度、社會階層、道德人品等無形的人格範疇與人生軌
跡。報刊的出現,似乎也映示女性公共再現時代的來臨。
當然,女性人物的移動,以及伴隨而生的際遇與身分流轉,並不
全然都是向上提升。《女獄花》與《俠義佳人》的女性流動,具正面
意義與價值者居多,具負面意義者也並非沒有。第二、三世代女作者
小說中,都不難發現這種現象。黃翠凝《姐妹花》曾經寫到出身貧寒
的女學生宋紅亭,利用拜訪同學的機會,憑藉美貌,結交富家子,意
圖攀緣婚姻,改善自己的生活階層, 後事與願違。28 這是存心不正,
自食惡果的故事,卻也折映了傳統女性流動的另種可能。婚姻,不但
是眾多女子的人生目標,也是改換處境、提升階層的動因、途徑。呂
韻清〈金夫夢〉描述女主人公「佩秋」的婚姻故事,29 其流離曲折,
雖非全然出於主動選擇,卻須自嚐苦果,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小說以倒敘手法寫作,「佩秋」青年美貌,卻孤身一人在濮院,
業織工維生,原來她曾經歷過一番變故,小說開篇兩句題辭:「兒女
27 〔清〕王妙如,《女獄花》,第 12 回,頁 756-759。 28 黃翠凝,《姐妹花》(上海:上海改良新小說社,1914 年再版),第 6 至 11 章,頁 19-40。 29 呂韻清,〈金夫夢〉,《春聲》第 2 期(1916 年 3 月 4 日),頁 1-18。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51
何關家國事?姻緣偏誤亂離中」,30 可以概括佩秋的遭遇。佩秋是浙
江人,浙江故里,是她的生長地,也是議婚訂親,擁有正常婚姻與身
分的地方。辛亥起義,城內動盪,夫家想要迎娶並下鄉避難,不巧佩
秋的父母重病,家中事務仰賴佩秋一人。佩秋不能出嫁,夫家避兵離
城,佩秋於是與夫家斷了消息,31 這是佩秋人生轉折的起點。政權移
易,造成動盪,人民為逃避兵亂而移動,也因此導致人生軌道的偏移。
具體物理空間的移換,牽連抽象人生界域的更替,其變化、發展難以
逆料,這是小說所要傳達的意義之一。李起文原是入獄黨人,因武昌
起事,從階下囚轉變為軍中英雄。佩秋的母親與兄長,受到李氏身分、
地位的吸引,慫恿佩秋改嫁,舉家前往上海。一到上海,佩秋果然改
嫁李氏。32 不但違背原有的婚姻信諾,而且事後才發現李氏另有大
婦,佩秋的身分不是正妻,只是小妾,她的婚姻與地位都失去了保障。
上海,這個興起於晚清、兼具殖民性與國際化的都會,在不少清末民
初小說中,是充滿活力生機,也是處處隱藏陷阱危機的城市。佩秋的
身分與人生,在此地誤入歧途,具有十足的隱喻意義。為了躲避正妻,
佩秋隨李氏遷居漢陽,到了漢陽,又發現李氏另有兩位小妾,一為女
優,一為流妓。佩秋出身良家,與二女同居,益覺抑鬱憤懣。接著李
氏入津京,不久因黨禍伏誅,二女捲資逃逸,佩秋隻身無依,勉強返
回浙江故里,母親已然亡故,昔日未婚夫也另娶新婦。33 出外繞了一
圈的佩秋,不但失去丈夫、母親,而且身分不明,既不是正式的寡婦,
也不是在室的女兒,既無婆家可依,在娘家也覺尷尬,於是跟隨妗氏
到濮院,靠織工為業謀生, 後安身的身分是女工。小說對於佩秋的
遭遇極表同情,佩秋對於自己的人生變換,除了哀怨,也滿是愧悔。
30 同前註,頁 1。 31 同前註,頁 1-7。 32 同前註,頁 8-10。 33 同前註,頁 11-18。
清華 學報
352
她的移動歷程,伴隨背婚改嫁的道德瑕疵,受人矇騙的不幸際遇,權
勢死生的命運無常, 早的起點則是時局動盪──大時代與小兒女的
關涉糾葛,歷經一番曲折, 後著落於自力維生的女織工。小說中,
她的移動主要出於各種不得已的被動因素,出嫁與否,主要受家人與
時勢的推促,嫁給李氏以後,又只能跟隨李氏流蕩,展露了女性人物
與世界互動時的無力與無奈,與前述積極主動的女性人物恰為對比。
民初多位女作者小說中,這類出於被動而移徙的女性人物,與主動出
走、遊歷的女性人物,互見春秋,顯出新舊雜陳、主客參差的斑駁姿
影。女性的主體與客體位置,穿插交織,映現女權發展階段中過渡時
期的實然特色。柳佩瑜(?-?)〈蕭郎〉(1914)、呂韻清〈白羅衫〉
都有這種表現。上述故事中,佩秋由正妻淪為小妾,其次喪夫,又次
淪為女工,身分轉換被描述成每況愈下,層層墮降,女工自食其力的
經濟獨立面向反隱而不彰。此中默默流漾的,是對女性身分的傳統判
凖,對於「女工」這個晚清新興職業身分的價值則並不看好。許毓華
(1900 前?-1957)〈一聲去也〉(1914)也見到這種傾向。羅蘭為貼
補生計,原在工廠當女工,認識陸生以後,便辭去工作。34 相較於上
述女教員、女醫師、女報人、女會長、女書記等各種事業女性,女工
顯然不是小說願意鼓勵的職業婦女。此中牽涉社會階層、地位尊卑、
男女有別等潛概念,凌越婦女經濟獨立的現實議題。婦女能否獨立自
主的問題,有時候,重要性比不上婚姻問題。
從某一面向看,女性人物的移動,夾帶強大的主體動能,積極迎
向並參與世界,擴展了行動空間與人生輻圍,也提升了自己的身分、
階層、地位與個體價值。從另一面向看,女性人物移動範圍、界域雖
然擴大了,卻依舊受困於既定的客體位置,被動沈浮於現實與際遇之
中,且蘊含無能為力之感。當被動與無力居於主宰位置之時,女性身
34 許毓華,〈一聲去也〉,《眉語》第 1 號(1914 年 11 月),冊 1,頁 14-15。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53
分地位也往往逐次遞降,呈示了移動的不穩定性及危機感。在清末民
初這個女權與現代性皆逐漸開展,傳統觀念與規範卻依舊深重的時
期,移動的意義與價值,仍處於肯定與疑慮交雜、正面與負面並陳的
多元交會狀態。同時,此中主客問題也顯得糾葛複雜。
四、從刻本到報刊:女作者及其小說的公共再現
小說想像的世界可以無遠弗屆,現實界的女作者卻只能一步一腳
印的蹣跚前行。當小說中女性人物輕快且堂皇的跨洋越洲之時,文壇
上女作者的身影其實還相當朦朧。
已知現存 早的女作者小說,是顧太清《紅樓夢影》,於光緒三
年(1877)由北京聚珍堂出版。根據魏愛蓮(Ellen Widmer)的考察
與推斷,原屬傳統出版商的北京聚珍堂,從 1876 年開始,有意識的
出版小說及其他遊戲性質書籍,順應了當時出版市場的變化,也響應
新時代的潮流,使《紅樓夢影》「成為十九世紀即將結束時,小說日
漸重要及其出版商品化的重要標誌」。「如果没有這種圖書市場的變
化,顧氏小說可能永遠不會出版」,「那樣的話,《紅樓夢影》便與這
位十九世紀的中國女性作家擦肩而過,與 1844 年以前汪端的《元明
逸史》、鐵峰夫人的《紅樓夢覺》同樣命運了。」35 魏愛蓮的考察極
為仔細,新的圖書市場與出版文化,催生了現今 早的女作者小說。
小說市場的逐漸繁盛,也預告了新的文學版圖的形成,以及更多女作
者小說的問世。《紅樓夢影》出版之時,並沒有提示作者的女性身分,
出版商自己很可能對作者也完全陌生,至少並不重視。此書書名頁署
「雲槎外史新編」,內有「西湖散人」序文一篇,每回回目下則題「西
35 [美]魏愛蓮著,毛立平譯,〈《紅樓夢影》及其出版商北京聚珍堂〉,收入《清史譯叢》(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9 輯,頁 279-295。
清華 學報
354
湖散人」撰,36 可見書商刻印之時,已經將「雲槎外史」與「西湖散
人」(沈善寶)混為一談。其實顧太清、沈善寶都是當時小有名氣的
女詞人、女詩人,「雲槎外史」是顧太清習用名號之一,37 小說署名
並未刻意隱藏作者性別與身分,然而當時認識她、知道她的,恐怕僅
限於曾經結社、唱和往來的親族友朋──例如替《紅樓夢影》寫序的
「西湖散人」沈善寶,屬於小眾團體而已。《紅樓夢影》出版這一年,
顧太清大部份時間仍在世(卒於十一月初三日,年七十九),38 小說
作者即便在世,知道的人卻顯然有限,讀者很可能根本未曾意識到這
部小說的作者是一位女作者。同時,小說實際出版年,距離沈善寶作
序的時間已長達十六年,39 當時小說的地位一向被輕視,小說作者大
部分不願或也不能以此名世。寫作與出版的時間相隔這麼久,可以
說,從某個側面反映了小說不受重視的景況。由於作者名號不為讀者
所識,這部小說對於顧太清的寫作事業與文壇聲譽而言,無論正面或
負面,恐怕都發揮不了什麼作用。小說出版,雖然是將作品公諸於世,
但女作者的身分並未揭曉,她的小說也只是芸芸通俗讀物或文化商品
之一種,沒有引起文壇注意。
《女獄花》的作者王妙如,在小說寫成以後、尚未出版之前便已
謝世,她的丈夫羅景仁以「體厥遺志」的態度,找人寫序,幫她的小
說刊刻出版。40 此書扉頁附有「王妙如像」,算是替亡妻留下紀念。
36 北京聚珍堂版《紅樓夢影》,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古本小說集成》之所本。[清]雲槎
外史(顧太清),《紅樓夢影》,扉頁書影、序文頁 1-3、正文頁 1。 37 〔清〕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前言〉,《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8 年),頁 1;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頁 165-
167。 38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頁 30。 39 〈紅樓夢影序〉署年為「咸豐十一年(1862)」,距離小說正式出版(1877),前後共計十六
年。[清]雲槎外史(顧太清),《紅樓夢影》,序文頁 3。 40 羅景仁,〈跋〉,收入王妙如,《女獄花》,頁 760。又,此書刊本並未標記出版商,很可能是
羅景仁自行籌資刊印。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55
刊登女作者肖像的做法,從某個面向看具有相當的前衛性,但此時卻
不是出於作者親手編印,就像李伯元逝世以後,雜誌上刊出他的小
照,41 意在替亡者留下音容,從另個面向看,這其實是很制式的一般
做法。根據羅景仁的跋文,王妙如嗜讀「書史」,生平著述除了小說
《女獄花》,還有《小桃源》傳奇、唱和集詩詞等,42 可見具備傳統
閨秀作家的文學素養。《女獄花》雖趕上「新小說」的出版潮流,得
以在成書後迅速公開面世,但英年早逝的女作者卻已經退出文壇與人
生舞台,作家無緣親見自己小說梓行,小說出版後評價如何、暢銷與
否,對女作者也失去意義。
黃翠凝《姐妹花》於 1908 年由上海改良小說社刊行,出版社以
「改良」為名,宣示了呼應梁啟超革新小說訴求的態勢。此時小說市
場已然大盛,黃翠凝也有賣文求活的經濟需求,譯、著小說屢屢署名
「番禺女士黃翠凝」,以真實姓名與性別身分示人,絕無意藏頭露尾。
但具有寡婦身分的她,投稿給小說雜誌,還是透過兒子送稿,43 可見
在實際文壇上仍不輕易拋頭露面。她的小說,既有由出版社刊印單行
本的長篇,也有刊登於小說雜誌的短篇,作者本人或許不太為人所
知,但婦女的文字作品公開面向大眾讀者,已然構成事實。
《俠義佳人》初集二十回,於 1909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
是當時走在現代化潮流前端、規模也數一數二的出版機構,一向關注
小說與教科書的編輯、出版,《俠義佳人》初集署名「績溪問漁女史」,
44 似乎帶有探問文壇消息的姿態,一年多後中集二十回續出,署名則
為「績溪勞邵振華」,45 已經坦然註記真實姓名。她的小說後來曾經
41 〔清〕吳趼人等編,《月月小說》第 3 號(1906 年 12 月),圖畫欄。 42 羅景仁,〈跋〉,收入王妙如,《女獄花》,頁 760。 43 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23-26。 44 績溪問漁女史,《俠義佳人》(上海:商務印書館,宣統元年〔1909〕4 月初版),初集,頁
1。 45 績溪勞邵振華,《俠義佳人》(上海:商務印書館,辛亥年〔1911〕7 月初版),中集,頁 1。
清華 學報
356
得到胡適的讚譽,46 但當時她的文名似乎不見響亮。辛亥鼎革,似乎
中斷了她原訂的寫作計畫,進入民國紀元以後,她不但淡出小說界,
很可能也謹守主婦範閾。47 此書的出版速度,可以說比寫作速度還
快。初集前附〈俠義佳人自序〉一篇,署「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孟
冬月」,48 實際出版為「宣統元年四月」,可見初集二十回寫完以後,
幾個月內就完成付梓印行。第二十回回末宣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
中集分解。」49 但實際出版則延遲到將近兩年後,可據此推測,當時
很可能還沒寫或至少沒寫完。中集第四十回回末也寫道:「欲知後事
如何,且聽後集分解。」50 但後集始終未見出版,推測應該是作者沒
有繼續寫下去。小說寫作與出版的速度如此緊密結合,主要因素當是
小說市場的需求迫切,出版商品化的動力,促進了小說出版的速度,
也讓女作者之小說寫作與公開面世的時程大幅縮減。不過此時大量的
小說刊載與出版,也容易讓作者湮埋於浩瀚的書林書海中。黃翠凝與
邵振華都以女作者的名號投稿、出版,當時也都健在,她們的小說雖
然有人讀,作者本人的文學活動與文壇聲譽卻顯得相當寂寥。
簡約的說,第一、第二世代的女小說家,都未以小說名世。顧太
清的女作者身分,當時很可能沒人注意。第二世代的女作者,不論出
於經濟因素,或出於關注女權問題,她們的小說雖經正式出版,黃翠
凝的姓名與作品還曾經分別登上晚清著名雜誌《小說林》與《月月小
說》的版面,不過,對於她們自身的寫作聲譽或文壇知名度,似乎並
未產生明顯提升作用。認識她們的人不是沒有,例如當時的編輯包天
46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者──《清閨秀藝文略》序〉,《胡適作品集‧三百年中的女作者》
(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冊 14,頁 168。 47 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1-16。 48 績溪問漁女史(邵振華),《俠義佳人》,頁 86。 49 同前註,頁 326。 50 同前註,頁 699。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57
笑,51 但除了小說本身的刊登與出版,文壇上,她們個人似乎並不活
躍,對於她們的作家身分,讀者似乎也沒有太多關注。羅景仁的跋文,
把王妙如描述成一個痛心女界黑暗的女權志士,52 邵振華的自序,也
強調自己親見親歷女界黑暗,為此感到痛心、不平,小說寫作的動力
即肇因於不平之鳴。53 關於這兩位女作者的寫作形象,無論被他人刻
畫或自我形塑,都凸顯了淑世啟蒙、有益社會家國的宗旨,54 歸屬於
傳統知識份子經世濟民以及晚清當時啟蒙救亡的主流價值。由追求菁
英文化、美感情趣、小眾傳閱的閨秀詩詞,轉變為啟迪蒙昧、鼓吹改
革、面向大眾的社會小說,女作者的寫作之路算轉了一個大彎,女作
者的形象也從閨閣才女轉型為參與社會議題、共同擔負時代使命的新
式知識婦女。清末提倡改革的政治社會思潮、女權學說的倡揚、啟蒙
救國的文學使命、圖書出版的新趨勢、小說稿酬的新機制等等因素,
共同支撐了這樣的轉折。更重要的是,這個轉折使女作者及其作品走
出閨閣與特定的小眾閱讀群,有機會公開面向讀者大眾,在寬闊的文
學市場佔有某個位置,也在文學版圖上擁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即便多
數讀者對作者的身分仍不關注或不熟悉,女作者已經突破長久以來
「內言不出」或「女子弄文誠可罪」的規範限制與罪責壓力,緩緩成
為公開文壇上正式的一員──女作者千年未有的移動,正在發生!
與此同時,邵振華曾以代表女界的姿態自我批評:
夫男子之敢施其凌虐,而吾女子之所以甘受其凌虐者,何也?
51 包天笑曾在自己主編的雜誌與晚年的回憶錄上分別提到黃翠凝。包天笑主編,〈離雛記〉,《小
說畫報》第 7 期(1917 年 7 月),篇前小引,頁 1;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縣:龍
文出版社,1990 年),頁 428-429。 52 羅景仁〈跋〉文說她認為「女界黑暗已至極點」,為了「普救眾生」,於是藉筆墨「為棒喝
之具」。羅景仁,〈跋〉,收入王妙如,《女獄花》,頁 760。 53 績溪問漁女史,〈俠義佳人自序〉,《俠義佳人》,頁 85-86。 54 《女獄花》的女主人公之一名叫「許平權」,《俠義佳人》中「曉光會」會長名叫「孟迪民」,
期許男女平權、啓迪民眾的寄意顯然可辨,女作者的自我期許與嚮往也託寓其中。
清華 學報
358
其中蓋有故焉:一則男子以為吾女子膽小如鼠,雖受其凌虐,
必不敢舉而暴諸世;一則吾女子性懶如貓,事事仰賴於人,雖
受男子之凌虐,而不敢訴於世。積是二因,逐成惡果。去之不
能,拔之不得,輾轉相承,演成今日之黑暗女界。其中男子雖
為禍首,抑吾女子豈無過歟?55
如此言論立場,往好處說是自我反省,往壞處說則是自我否定。「膽
小如鼠」或「性懶如貓」的說詞,不全然是同情的表態,有更多敵視、
排斥的意味含藏其中。字面上雖稱男子為「禍首」,但實際上「不敢
訴於世」或「暴諸世」的主角都是女人,責怪男子的同時,自我貶責
的意味甚至更為濃厚。王妙如也在《女獄花》中批判婦女無知無能,
甘做奴隸。小說曾藉沙雪梅之口痛罵男子為「男賊」,又藉許平權之
口,在女學堂的開學演說上長篇大論,強調「女人的弱點在於依賴性
質」,「將恨男子強權的心思,變為恨自己無能的心思」等等。56 痛罵
「男賊」的橋段,雖然表現得似乎頗為憤慨,但是長篇大論宣導女權
學說的內容,卻也充滿了責怪女子自己不爭氣的批判。「女界黑暗」
的論調,不僅僅指出婦女的受難苦境,也同時責備婦女自身的能力與
行為。女作者對於身為女人,除了自嘆不幸,57 也在字裡行間自我反
省、責備或排斥。這種姿態似乎洩漏了長期遭受貶抑的婦女自信不
足,面對窒礙窘境時,自責多於責人的幽曲心理。女作者對於自己的
權益與份位,猶疑不定甚或否定的成分仍多於正面肯定。
第三世代女作者小說中,救拔女界黑暗的議題大幅退場,言情說
愛的題材躍居主流,小說刊登與作者現身的方式也明顯改變。時勢轉
移帶來的各種變化,在小說文本外部與內部,都可以看到不少蛛絲馬
55 績溪問漁女史,〈俠義佳人自序〉,《俠義佳人》,頁 85。 56 [清]王妙如,《女獄花》,第 3、11 回,頁 721、753-755。 57 績溪問漁女史曾直言:「吾生不幸而為女子。」績溪問漁女史,〈俠義佳人自序〉,《俠義佳
人》,頁 85。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59
跡。《眉語》雜誌由高劍華主編,女作者主掌了發表園地。在女主編
的經營之下,總計十位女作者的照片,於前三期雜誌上輪番登場(詳
附圖一、二、三),後進的投稿者徐張蕙如,也以「眉語之友」的名
義,在第十一期刊出小照。58 主編高劍華前後至少刊登過六張照片,
包含三張獨照,三張合照,59 其中一張是新婚旅行的夫婦合照,一方
面分享私人生活,一方面彰顯新式婚禮的時尚流行。姚淑孟也刊登過
一張獨照、一張夫妻合照。60 女作者樂於或勇於亮相,表現大方公開
的新女性姿態,足見不輕易拋頭露面的傳統婦訓已然淡化。其實從清
末開始,便有不少先進婦女在報刊上登過照片,例如秋瑾、張竹君、
呂碧城等,「名女人」的意象逐漸凝塑。民初女作者刊登照片,仍屬
新潮,卻非前衛。橫跨第二、三世代的女作者呂韻清也在不同時期、
不同雜誌上刊登過至少三張獨照, 早刊出的一張,是清末發行的《女
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以「石門文明女塾女教員」的身分出現,
61 不論是出於對自己容貌的自信,或是應編輯之請,呂韻清此一不吝
展露玉容的作風,與《眉語》女作者顯然相當合拍。從《眉語》女作
者照片的取景可以發現,除了獨照肖像以外, 常見的是夫妻合影,
女作者以低於男子的姿位,或坐或站,手腳收束,表現嫻靜或依偎之
態(附圖一)。女作者獨照所選來搭配的器物與動作,有彈琴、看報、
58 《眉語》第一、二、三號圖畫欄,刊登了所有女編輯員與編撰員的照片,徐張蕙如照片見
於第 11 期圖畫欄,頁 7、8、402、2322。又,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的《眉語》
第二號「圖畫」欄所有圖片、照片均闕佚,據上海圖書館藏《眉語》原件補齊。 59 高劍華的六張照片分見於《眉語》第 1 號(1904 年 11 月)、第 2 號(1904 年 12 月)、第 3
號(1905 年 1 月),圖畫欄。文末附圖為夫妻合照,使用(上海)新學會社出版的原刊本。 60 高劍華主編,《眉語》第 3 號(1905 年 1 月)、第 13 號(1905 年 11 月),圖畫欄,頁 420、
2784。 61 〔清〕常熟女子世界社編,《女子世界》第 12 期(1905 年 4 月),圖畫欄。按、此處圖畫取
自上海圖書館藏原刊本。又,《女子世界》雖稱月刊,發行時間卻不穩定,此處的發行年月,
是根據夏曉虹考察及推測而得。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晚
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9。
清華 學報
360
採花,展露新式藝文素養或日常生活意趣(附圖二)。比較特別的是
孫青未,背對著鏡頭,全身卻在一面長鏡子(很可能是當時的「穿衣
鏡」)裡面映照出來(附圖三)。62 這個鏡中之相頗具隱喻效果,出現
於《眉語》雜誌上的女作者,除了高劍華有多量的寫作與編輯作品流
傳下來,徐張蕙如在其他雜誌也刊登過作品以外,其他女作者不但作
品數量少,而且未曾在其他雜誌或出版物上出現。她們是文壇上壽命
甚短的曇花、稍縱即逝的鏡中影。《眉語》上這些作品數量不多,也
未見在其他雜誌上發表的女作者,很可能多數是高劍華的同學、親
友,63 由於高劍華擔任主編的緣故,被邀請投稿。雖然不少女作者的
寫作生涯相當短暫,但是她們的小說加上照片,文字文本與作家本人
的肖像同步流播,公開面對廣大的讀者,其開放性更進一步,自我認
同與肯定的程度也更高。
《眉語》是現存少見、也很可能是中國史上第一份女編輯主編的
文學雜誌,雜誌上容納了前所未見的、多量的女作者小說,雜誌本身
還曾以「閨秀之說部」為號召。64 清末民初的女小說家個別投稿或出
版是常態,《眉語》雜誌以女編輯為主力,集結了多位女小說家的事
實,無異宣示女作者在文壇上更進一步的作為,至少是企圖掌握更多
發聲權、發揮更多主體性動能的嘗試。女作者的群聚方式,由親族友
朋之間、庭闈室院之地的詩詞結社,移位到公開面向大眾的報刊雜
誌,且公開徵求刊載品,65 接納來自四方的其他作者,這是文學史與
婦女史上破石驚天之舉!長期處於邊緣位置的女作者,透過雜誌的運
作,以更為自主公開的方式,向讀者大眾展示自己的文字與相貌,宣
62 高劍華主編,《眉語》第 1 號(1904 年 11 月)、第 2 號(1904 年 12 月)、第 3 號(1905 年
1 月),圖畫欄。按、此處圖畫均取自上海圖書館藏新學會社原刊本。 63 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221-225。 64 郭浩帆,〈民初小說期刊《眉語》刊行情况考述──以《申報》廣告為中心〉,《學術論壇》
2015 年第 1 期,頁 101-106。 65 《眉語》曾經透過廣告,公開徵求婦女照片、墨寶、文稿等。同前註,頁 104。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61
告自己的身分與定位,女作者的自我醒覺,意義非凡!
民初開始,女作者小說大部分都曾刊登在各種雜誌報刊上,尤其
是短篇小說,《眉語》雜誌只是較為集中刊載了女作者小說的一種。《眉
語》女作者群之外的呂韻清,有兩種以單行本出版的長篇小說,其他
短篇小說九種66 則分別刊載於不同的報刊雜誌上。呂韻清是此時少見
的另一位多產女小說家,以作品篇數而言,在清末民初三個世代女作
者裡面,可謂獨佔鰲頭。她的作品遊走在各種不同的雜誌報刊上,包
括《七襄》、《女子世界》67、《小說叢報》、《繁華雜誌》、《小說大觀》、
《春聲》等(詳附錄一),投稿相當活躍,照片則分別刊登於清末常
熟女子世界社、民初天虛我生所編的兩種《女子世界》與《香豔雜誌》,
68 是一位能見度頗高的女作者。呂、高等人的自我再現,已然有別於
上一世代的邵、王等人。
報刊雜誌成為女作者發表小說、現身文壇的重要方式,是不可忽
視的一項信息。報刊發表的開放性與公共性,遠非第一世代的「雲槎
外史」與《紅樓夢影》所可比擬,更非傳統詩詞閨秀或以婦女為主要
閱聽群的彈詞女作者所能想像。進入公共領域,可以說是婦女歷史上
的一大步,不僅僅在物理空間上跨出閫域,也在抽象空間裡進行各種
可能的開拓。從清末民初三個世代女小說家的寫作與發表軌跡,可以
觀察到婦女之身心移動、界域之立體擴張的長足發展,這是發生於十
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婦女寫作歷史上千年未有的移動現象!雖然
整體來說女作者依然處於邊緣位置,但是已經可以見到逐漸向文學版
66 呂韻清發表於報刊雜誌的小說,計有十二篇,但其中兩篇是異名同文,一篇是重複發表,
故實際上為九種。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頁 82-83。 67 清末民初有兩種同名為《女子世界》的雜誌,清末者為常熟女子世界社所辦,民初者為天
虛我生(陳蝶仙)所辦,此為民初天虛我生(陳蝶仙)所辦。 68 〔清〕常熟女子世界社編,《女子世界》第 12 期(1905 年 4 月),圖畫欄;天虛我生(陳蝶
仙)編,《女子世界》第 3 期(1915 年 3 月),圖畫欄;《香豔雜誌》第 4 期(1914 年 12 月),
圖畫欄。按、此處圖畫均取自上海圖書館藏新學會社原刊本。
清華 學報
362
圖中心邁進的足跡。
五、結語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發現清末女作者小說的敘事空間,大體是
「內」重於「外」。女作者不但有偏好室內空間的傾向,而且演繹出
家內空間的多元面向與複雜意義。女作者小說中的空間流動少數屬於
不頻繁,多數仍相當頻繁,而且第二個世代女作者小說的流動版圖擴
及海內外,顯現出受到西化與女權思潮的影響,以及女作者亟欲走出
閨閣、向外拓展的意願。只不過,室外空間的流動敘述大都偏於簡略、
以省筆帶過,甚至夾帶危險、不安的疑慮,隱示女作者們對於室外空
間的畏卻、憂懼。換句話說,傳統男外女內的思想,以及社會或公共
空間既存的對女性之不友善待遇,仍然深深影響女作者的空間意識與
感知。民初女作者小說的敘事空間大幅向室外拓展且流動,女作者本
身有不少隻身外出、遠行的實際經驗,女性移動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逐
漸加強,移動的主體動能也漸次顯現。同時,女作者樂於以刊登小照
的方式,在報刊雜誌等媒體空間再現自我圖象,其自我認知與主體意
識已經明顯提升,也更勇於或樂於參與社會與世界。
(責任校對:朱芯儀)
清華 學報
366
附錄一:十五位女作者及其小說詳目
編號 姓名 (生卒年)
小說名 出版或 發表處
初刊年代
1 雲槎外史(顧太
清)(1799-1877) 《紅樓夢影》二
十四回 北京聚珍堂版 光緒丁丑
(1877)
2 王妙如(1878?
-1904?) 《女獄花》十二
回 未標明 光緒甲辰
(1904)刊本
3 績溪問漁女史(邵
振華)
(1881-1924)
《俠義佳人》四
十回(初集二十
回,中集二十回)
(上海)商務印
書館 初集宣統元年
(1909)四月
初版,中集辛
亥年(1911)
七月初版
4 黃 翠 凝 ( 1875 ?
-1917 後) 《姊妹花》十一
章 (上海)改良小
說社 光緒三十四年
(1908)刊行
〈猴刺客〉 《月月小說》第
21 號(週年紀典
大增刊)
戊申(1908)
九月
〈離雛記〉 《小說畫報》第 7號
1917 年 7 月
5 呂 韻 清 ( 1870 ?
-1937 後) 〈淩波閣〉 《七襄》第 2 期 1914 年 11 月
17 日
〈狸奴感遇〉 《七襄》第 3 期 1914 年 11 月
27 日
〈白羅衫〉 《七襄》第 5、6期
1914 年 12 月
17、27 日
〈秋窗夜嘯〉 《女子世界》第 3期
1915 年 3 月 5日
〈彩雲來〉 《小說叢報》第
10 期 1915 年 4 月 30日
〈蘼蕪怨〉 《繁華雜誌》第 5期
1915 年
〈花鏡〉 《小說大觀》第 4 1915 年 12 月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67
編號 姓名 (生卒年)
小說名 出版或 發表處
初刊年代
集 30 日
〈金夫夢〉 《春聲》第 2 期 1916 年 3 月 4日
〈紅葉三生〉 《春聲》第 5 期 1916 年 6 月 1日
《石姻緣》 (上海)文明書
局 1917 年 2 月
《返生香》十四
回 (上海)廣益書
局 1938 年
6 高 劍 華 ( 1890 ?
-1947 後) 〈處士魂〉 《眉語》第 2 號 1914 年 12 月
〈春去兒家〉 《眉語》第 3 號 1915 年 1 月
〈裸體美人語〉 《眉語》第 4 號 1915 年 2 月
〈劉郎勝阮郎〉 《眉語》第 7 號 1915 年 5 月
〈繡鞋埋愁錄〉 《眉語》第 9 號 1915 年 7 月
〈蝶影〉 《眉語》第 10 號 1915 年 8 月
〈裙帶封誥〉 《眉語》第 12 號 1915 年 10 月
《梅雪爭春記》
十三回(未完)
《眉語》第 13 至
18 號 1915 年 11 月
-1916 年 4 月
〈賣解女兒〉 《眉語》第 14 號 1915 年 12 月
7 許毓華(1900 前?
-1957) 〈一聲去也〉 《眉語》第 1 號 1914 年 11 月
8 馬嗣梅(?-?) 〈 繡 鞋 兒 剛 半
折〉 《眉語》第 1 號 1914 年 11 月
9 梁桂琴(?-?) 〈一朝選在君王
側〉(參輯對山筆
記)
《眉語》第 1 號 1914 年 11 月
10 梁桂珠(?-?) 〈同氣連枝〉 《眉語》第 2 號 1914 年 12 月
11 柳佩瑜(?-?) 〈蕭郎〉 《眉語》第 2 號 1914 年 12 月
清華 學報
368
編號 姓名 (生卒年)
小說名 出版或 發表處
初刊年代
〈才子佳人信有
之〉 《眉語》第 5 號 1915 年 3 月
〈郎情如水〉 《眉語》第 12 號 1915 年 10 月
12 謝幼韞(?-?) 〈他生未卜此生
休〉 《眉語》第 3 號 1915 年 1 月
13 姚淑孟(?-?) 〈郎歟盜歟〉 《眉語》第 3 號 1915 年 1 月
14 孫青未(?-?) 〈儂之心〉 《眉語》第 3 號 1915 年 1 月
15 徐張蕙如(?-?) 〈珀釧女兒〉 《眉語》第 10 號 1915 年 8 月
〈洗炭橋〉 《眉語》第 11 號 1915 年 9 月
〈韓牛〉 《眉語》第 12 號 1915 年 10 月
〈麗娘慘史〉 《眉語》第 16 號 1916 年 2 月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6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顧太清、奕繪著,張璋編校,《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清〕雲槎外史(顧太清),《紅樓夢影》(1877),收入古本小說集成
編委會編,《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冊 44。
〔清〕單士釐,《癸卯旅行記》(1904),日本同文印刷舍印本,收入
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1985 年,冊 5。
〔清〕王妙如,《女獄花》(1904),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說
大系》,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冊 64。
〔清〕常熟女子世界社編輯,《女子世界》第 1 至 17 期,上海:大同
印書局、小說林社,1904-1906 年。
〔清〕吳趼人等編,《月月小說》(1906-1909),第 1 至 24 號,上海:
月月小說社。上海:上海書店,1980 年重印,全六冊。
番禺女士黃翠凝著,《姊妹花》(1908),上海:上海改良新小說社,
民國 3 年(1914)10 月再版。
績溪問漁女史(邵振華),《俠義佳人(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
宣統元年(1909)4 月初版。
___,《俠義佳人(中集)》上海:商務印書館,辛亥年(1911)7
月初版。
___,《俠義佳人》(1909-1911),收入王繼權等編,《中國近代小
說大系》,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冊 64。
高劍華主編,《眉語》(原刊本)第 1 至 18 號,上海:新學會社,1914-
1916 年。
___,《眉語》(1914-1916),收入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民
清華 學報
370
國珍稀期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6 年。
七襄社編,《七襄》第 1 至 9 期,上海:七襄社,1914-1915 年。
天虛我生(陳蝶仙)編,《女子世界》第 1 至 6 期,上海:中華圖書
館,1914-1915 年。
徐枕亞主編,《小說叢報》第 1 至 21 期,上海:小說叢報社,1914-1917
年。
海上漱石生(孫玉聲)主編,《繁華雜誌》第 1 至 6 期,上海:錦章
圖書局,1914-1915 年。
包天笑主編,《小說大觀》第 1 至 15 期,上海:文明書局,1915-1921
年。
姚鵷雛編,《春聲》第 1 至 6 集,上海:文明書局,1916-1917 年。
包天笑主編,《小說畫報》第 1 至 22 號,上海:文明書局,1917-1920
年。
呂韻清,《石姻緣》,上海:文明書局,1917 年。
___,《返生香》,上海:廣益書局,1938 年。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臺北縣:龍文出版社,1990 年。
二、近人論著
〔法〕帕特里斯‧伊戈內(Patrice Higonnet)著,喇衛國譯,《巴黎
神話:從啟蒙運動到超現實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美〕魏愛蓮(Ellen Widmer)著,毛立平譯,〈《紅樓夢影》及其出
版商北京聚珍堂〉,收入《清史譯叢》第 9 輯,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2010 年,頁 279-295。
〔英〕彼得‧艾迪(Peter Adey)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移動》,
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德〕梅嘉樂(Barbara Mittler)著,孫麗瑩譯,〈挑戰/定義現代性:
上海早期新聞媒體中的女性(1872-1915)〉,收入游鑑明、羅梅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71
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臺北縣:左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07 年,頁 255-287。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
說總目提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 年。
呂芳上,〈五四時期的婦女運動〉,收入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
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年,頁 157-254。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者──《清閨秀藝文略》序〉,《胡適作品集‧
三百年中的女作者》,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冊 14。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晚清女性
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張菊玲,《曠代才女顧太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年。
郭浩帆,〈民初小說期刊《眉語》刊行情况考述──以《申報》廣告
為中心〉,《學術論壇》2015 年第 1 期,頁 101-106。
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者小說研究》,臺北:
里仁書局,2014 年。
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長
沙:岳麓書社,1985 年,頁 657-679。
清華 學報
372
Space, Identity and Public Re-presentation: The “Mobility”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1840-1919) Women Writers
Jin-chu Huang
Abstract
The newly-introduced idea of “women’s right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xerted a great impact on women writers, causing them to
step out of their confined inner chambers and into a new territory for
individual personal development, which at the same time remained
paradoxically intertwined within the web of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ethical
and familial bonds. Fiction, a genre that had hitherto been seen as
peripheral and of low social standing, started to move upwards to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social milieu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At this
time, women, who had been excluded from mainstream, male-dominated
literary circles, began to gain recognition. Women writers not only gained
recognition, but they also started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that they never
had played before. What they wrote shifted from more esteemed genres
such as poetry, ci poems, prose, rhymed rhapsody, to less esteemed ones
such as popular fiction. In addition to a shift to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this “movement” signified a change in their conception of identity, the
ways in which their works were disseminated, and how authors presented
themselves. Interestingly,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space and th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空間、身分與公共再現:清末民初(1840-1919)女作者小說的「移動性」
373
movement that followed from it,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among women
writers also underwent a significant change, so much so that their intent
to take part in worldly affairs and to construct their selves found new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on in their writing. This indicates that a new
reality was appearing and that a new awareness of selfhood was
unfolding for them. These new ways of behaving within their new space,
the switching and flowing of identity, and a new self-image about who
they really were, all constitute a very important foundation from which to
investigate the worldview and self consciousness of thes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women writer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 fictional
works of fifteen women writers from this period to see how they move,
how they understand and relate their moving in the real world and in their
writings. It will also look into the birth of their fictional texts as well as
how they were published and disseminated. In sum,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to explore the space consciousness, the worldview, the
gender recognition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women writer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second, to reflect on their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omen writers of
fiction, moving, space, identity, public re-presentation
Related Documents